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pure single-incision laparo-scopic surgery (pSILS)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The pSILS has advantages in minimally invasive and cosmetic procedures, but it requires high surgical techniques and has limitations. The Robotic and Laparoscopic Surgery Committee of Chinese Research Hospital Association and Editorial Board of the 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ive Surgery have organized domestic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experts to develope the
Expert Consensus on Surgical Procedure of Pure Single-incision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Gastric Cancer (2025 Edition) based 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clinical practice. The aim is to standardize the application of pSILS in gastric cancer treat-ment, improve surgical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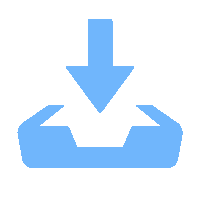 下载:
下载: